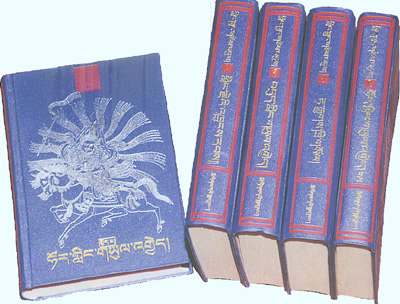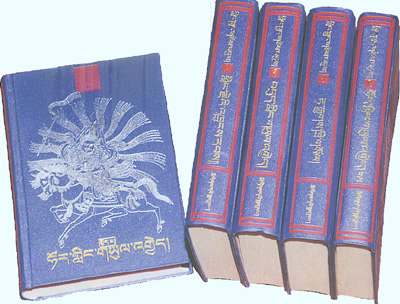
三
与对平等、公正、和平、安宁、幸福的社会追求相统一,由于藏族特殊的阶级关系,僧侣官员阶层是精神生产者,也是统治者,对他们来讲个体最高的德行便是“爱护黎民若子女”,引导众生走向佛陀,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个体的最高善行则是对佛的绝对虔敬、信仰以及勤劳、公利。而上述两个层次则构成了藏族社会美中特殊的创造观念。正是这种创造观念稳固了藏族社会的阶级关系,也正是这种创造观念创造了藏族特殊的审美文化。
《花岭诞生之部》中一开始便引用古代藏族人的谚语阐述其创造观念:“对于神灵、珠宝与官长/经常奉事心愿才能实现/对于买卖、农耕和家务/勤劳不怠才会增财产/对于马儿、妻子与房屋/随时装饰样子才美观。”(28)这一观念显然是从特定的角度对被统治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训导与劝戒,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广大下层藏族人民辛勤地劳动在农耕、牧场之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保证了藏族的种系繁衍和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包括审美文化)的传承。佛教倡导的基本行为规范之一便是“积极奋进”,即“勤”或“精进”。正是下层人民的劳动及财富才使得藏传佛教得以弘扬光大。《花岭诞生之部》中曾详尽记述了格萨尔在消灭了玛域地区的强盗土匪之后,过往的商人们既给格萨尔神子进贡、奉献物品,同时还被罚建宫殿与茶城。格萨尔曾对向他借地方的六位岭国使者骄傲地宣称:“那年拉达克商人贩货物/霍尔毒蝎五人来劫夺/我角如随后追赶去/强盗虽未被我捉/抛石却打死霍尔托托王/获得托桑巴尔瓦大铜锅/拿来九黄闪亮的托热剑/夺回拉达克商人不少商货/下行经商的众商客/我向他们抽商税/送我金银丝绸与马骡/这是我收税的第一回//汉地的茶商一千人/我们中间纠纷起/他们想抢我枣骝马/我将他们统统下监狱/他们不得不认输/茶砖一千块作献礼/还罚建宫殿与茶城/这是角如第二次得胜利。”(29)下层老百姓的辛劳显然是由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以及无奈的命运逼迫下的自觉选择。因此,勤劳、奉献等观念作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并进而灌输到老百姓的头脑,由外在的规范变成内在的自觉欲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从历史的观念看,它正构成了藏族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动力,成为藏族人民的一种美德。
与广大的下层劳动者不同,自从藏传佛教产生以后,就规定了僧侣阶层是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的,他们既是宗教代表,又是政治统治者,他们的吃、喝、住、穿、用等一切物质条件均由下层劳动者——农牧民提供。而这些“身披黄缎袈裟的修法人/吃着人间美味享清福/坐在舒适的金座上/还觉太苦不舒服/梦想进入极乐世……”(30)对于这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人们的最美好的企望便是他们能有一点善心,能够体恤老百姓的痛苦,能给老百姓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正如格萨尔的生母果萨拉尕尔向自己的父亲龙王所唱的那样:“听说上师喇嘛胸怀广/就象苍天空旷无边际/因此有话要向你讲/上师喇嘛你的想法是——/从佛典经续的乳海中/能将观修的精华来摄取/又把众生引向解脱路/好喇嘛善行应如此/好首领的行为应当是——/爱护黎民若子女/执法公正不偏私/能使百姓得安逸/如果能够这样做/才算首领有见识。”(31)格萨尔则一再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公利:“凡我所作所为,会是为了众生谋幸福。”“除了黑头藏人公利外,格萨尔王我无私利。”(32)甲擦协尕尔则提示格萨尔:“为了众人事/万死也不辞……/如果松懈麻痹/则会损害众生的安乐、幸福。”(33)而前述那些岭国英雄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也正是为了公利而不惜赴汤蹈火的具体表现。格萨尔大王更是为了公利忍受了超同的迫害,流落玛域,母子相依为命,挖蕨麻、捕地鼠、食猎肉——真有一种“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的悲壮,有一种“泥水当中生妙莲/要任其自然去萌发/太阳照它开花朵/无用把污泥去洗刷/但是谁也忘不了/淤泥浊水生莲花”(35)的哲理妙趣。而正是在苦难的磨炼考验中,格萨尔才真正奋起了,他终于成了“黑头藏人”的统治者、救世主,他给“黑头藏人”带来了光明、幸福与欢乐。
由此可见,藏族所强调的创造——勤劳、公利、爱民等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阶级、阶层所对应持有的两个不同层次、平面的创造活动。对于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来说,勤劳只意味着劳动力的付出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这种物质财富并不为劳动者本人所有,相反,在极其漫长的阶段里劳动者本人是没有支配权的。勤劳带给他的是贫困,付出也并不意味着收获、拥有。正如马克思据说的,“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宫殿,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36)藏族劳动人民的勤劳在现实的层面上实际被歪曲、异化了,它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当然得不到对象化。只是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具有强烈的信仰精神,而“政教合一”的特殊社会政治结构又通过政治的手段强化了宗教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在勤劳创造问题上有着自己特殊的观念、心理。藏族人民在劳动力及其物质成果上的付出,如纳税、布施、无偿的宗教性劳动,从其心理感受上说,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补偿”或“消费”活动,而非简单物质性的付出。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得到了某种心灵上的满足,并进一步促发着自己的幻想。藏传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一切无常,皆假非真,乐少苦多”,而只有在涅磐中才是“寂灭永乐”:“贪欲永尽, 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37)这种重来世、涅磐,而轻视现实生活的观念的理论基础则是因果报应的轮回业报学说。在它看来,来世涅磐是大乐大美的境界,现实只是生命循环轮回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有限、暂时、虚幻的,“一切皆苦”。现实的这一切都是爱及其欲望的摧动下产生的,而消除这种痛苦就要根除欲望以消灭爱,彻底地驱逐它、离开它,人们在现世只能也只应艰苦地忍受今生的各种苦难,行善积德。基于这样的认识,处在现实苦难中的善良的人们,几乎放弃了一切现实人世的享乐、荣辱、得失。对宗教的布施、花费、无偿劳动也就是为来世换取善果报应而作的一种努力、一种铺垫、一个筹码。企盼通过这种宗教的努力,求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佛的护佑,使自己从精神上、心理上超越现实有限,解除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愉悦和欢乐。由此,物质性劳动也就具有了情感——审美的色彩。
对于僧侣官员阶级来说,他们的公利——创造观念则又显然是建立在不证自明、天然合理地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肯定基础上的,因为根据佛教观念,他们是佛、神的化身、代表者,因而他们便始终以高于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惯性来思维。在他们那里公利、利他的活动从客观上固然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一件好事、善事,但从主观上讲,僧、官们首先是把这种创造行为作为一种仁慈、施舍、普济。他们是站在佛的高度,以一种超越世俗的大度居高俯视芸芸众生,他们所关注的人的创造当然更彻底的是精神性的。这里当然存在着超越功利的情感——审美感受。这些我以为正是藏族社会美思想独特的东西。
四
综观上述藏族社会美思想的具体观点,无论是对平等、公正、幸福、和平、统一的企盼向往,还是对人的创造——勤劳、公利的肯定追求,它们自身都并不自觉,相反,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更神圣、更高级的存在——佛,格萨尔大王即是佛之子,是佛的代表和化身。
在社会理想的层面上,平等、公正、幸福、和平、统一、勤劳、功利等都只有在佛即格萨尔大王的神性的统摄下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所谓社会美中的平等、公正、幸福、和平、统一都是相对的,是有前提的,即格萨尔大王允许、认可、倡导。而且这种平等、公正、幸福也主要是精神心灵性的,而非物质现实性的。只要得到格萨尔大王的认同、肯定,那即使自己纳税、受罚,在精神上是幸福、快乐的。如前所述,这是由佛教否定人生价值,轻视现实社会,提倡止恶行善,确认因果报应,主张来世幸福,向往佛国天堂的观念决定的。正是由于藏族执着地甚至不惜一切地追求一种终极理想,尽而超越了生死、贫富、得失、毁誉、荣辱、利害、是非等,只要是有益于自己成佛或接近佛的,他们便会认可,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据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格萨尔》中所倡导的各种观念的真正的内涵以及它对现代意义的自由观念的漠视,它所内含的社会美思想的特殊意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格萨尔》的社会理想时,它可能是虚幻、不切实际的,但从美学角度来看,其社会理想、社会观念却是富含审美精神的。因为,他们超越了物质利欲的现实世界,而指向一种终极性的精神性的目标,从而支撑藏族在漫长的数千年中承受住了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严竣考验,坚忍不拔地生存下来并走向现代。固然,藏族社会美的审美精神与藏族社会现代化的现实追求肯定并不是和谐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美思想价值的丧失。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对传统文化的频频回眸,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藏族史诗《格萨尔》所显示的传统社会美思想仍将不断显现自己特殊的价值,其对现世、人生的否定等缺失理所当然会得到扬弃。
————————————————
⑴《仙界遣使》,转自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第3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
⑵《霍岭大战》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⑶⑷⒄[23][24][25]《保卫盐海之部》第22、23、76、49、136页,青海民研会编印。
⑸⑹⑺⑻⑼⑽⒀⒇[21][22][31][32][33]《贵德分章本》第1、17、34-35、316、162、170、179、38、3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⑾⒁⒂⒃⒅⒆[28][29][30][35]《花岭诞生之部》第4、124、125、44、4、134-135、6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⑿[26][27]《卡切玉宗之部》第三产业18、6-7、10-12、1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4]《孟子•告子下》。
[3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第46页。
[37]《杂阿含经》卷十八。
*本文系甘肃省1997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